在中国创新药领域,由顶尖科学家亲自牵头,把世界领先的原始创新成果直接搬进企业做转化,炎明生物是极少数。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10月的一个上午,邵峰走进会议室,十几个化学、药学和生物领域的科学家正在等他。
作为全球细胞焦亡领域最顶级的科学家,邵峰有着中国科学院院士、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科研副所长等多个重量级头衔。不过,在这间办公室里,他的身份和其他人一样:炎明生物研发团队的一份子。
临近中午,散会,有人留了下来。年轻的研究员低头细语,半晌,邵峰详细回应疑问,又一字一顿告诉他:“你自己要有思考,要有坚持,要独立,不要去迎合别人。”
炎明生物,北京生命科学园里一家年轻的创新药企,2020年10月注册,邵峰任联合创始人、董事长,也是研发灵魂。
和目前绝大多数药企不同,炎明生物药物研发的核心不是针对已经被验证了的成熟靶点,而是来自针对最新科学发现的新靶点,做原始创新和原研新药开发,所有项目都建立在邵峰实验室重点研究的天然免疫和细胞焦亡机制上。
在中国创新药领域,由顶尖科学家亲自牵头,把世界领先的原始创新成果直接搬进企业做转化,炎明生物是极少数。依靠实验室十多年的积累和邵峰的深度参与,两年过去,炎明生物已经积累不少成果,但做成一款真正的创新药,至少还需要四五年。
“再要更快就不可能了。”邵峰说。
邵峰经常到公司参会,日常就在一公里外的北生所实验室工作,往返便利。
只是这一天参会,邵峰费了些周折——一个月前,因为在细胞焦亡领域的原创性发现,邵峰拿了威廉·科利奖,这是肿瘤免疫学界的顶级大奖,他受邀赴美领奖并做主旨演讲,回国后在上海、北京隔离3周。这间会议室是他解除隔离后的第一站。
会议室的角落里,一个中年人微笑地看着邵峰和同事交流。他叫邓天敬,是邵峰的合作伙伴,炎明生物联合创始人、CEO。他向等在一旁的经济观察报记者解释:“这样的科学问题,我们每天都在探讨。”
除了科学问题,邵峰和邓天敬之间的交流范围更加广泛,他们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做出由中国人发现靶点,并在世界上第一个上市的新药。这是一个高远的目标,通向的它的每一步要怎么走,是邵峰和邓天敬交流最多的问题。
闯关


邓天敬 炎明生物联合创始人、CEO
邓天敬觉得,做原始创新就像打仗。找好目标,定好战略,建好团队,备好粮草,剩下的事就是把好方向,带着战友去攻占山头。
2022年8月,炎明生物宣布,针对Gasdermin家族蛋白开发抑制细胞焦亡的全新药物分子项目,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特异性针对Gasdermin蛋白的抑制剂。从苗头化合物,到最终得到其和蛋白结合的高分辨结构,炎明生物只用了一年。另一个炎症项目,从高通量大规模筛选化合物到获得国际上第一个复合物共晶结构,也只用了半年多。
超过100人的团队在推进管线的研究。如今,炎明生物最快的项目已进入临床前的研究阶段,预计在2023年进入临床,还有多个项目进入IND Enabling阶段。
邓天敬告诉经济观察报:“管线各个项目的研发进度比想象中快多了。”
当然,困难也比想象中要多。
在制药领域,要做成第一个原创新药难度很大,没有对标和对照,就像在暗夜里摸索,每向前一步,都是人类迈出的第一步,这样的研发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努力,试错成本高,但价值也更高。
炎明生物的研发集聚了天然免疫和细胞焦亡中多个靶点和项目,最大程度分散了风险。
内部的投入再大,自己总可以把握,外部的困难却往往不由自己做主。
在美国的新药研发体系上,原创药物研发已经有了成熟的投资、监管、上市的生态;而在中国,这些都才起步,大家都在快速学习的过程中。
“这些年,大家熟悉的是那些同质化较高,跟随式创新的项目。对这样的项目,人们看有没有到临床二期、三期,觉得那才是创新药研发过程中的价值体现。但对从‘0’到‘1’的原始创新来说,它的价值其实在早期就能充分体现,这是国际惯例。这方面我们可能还需要观念改变。”邓天敬说。
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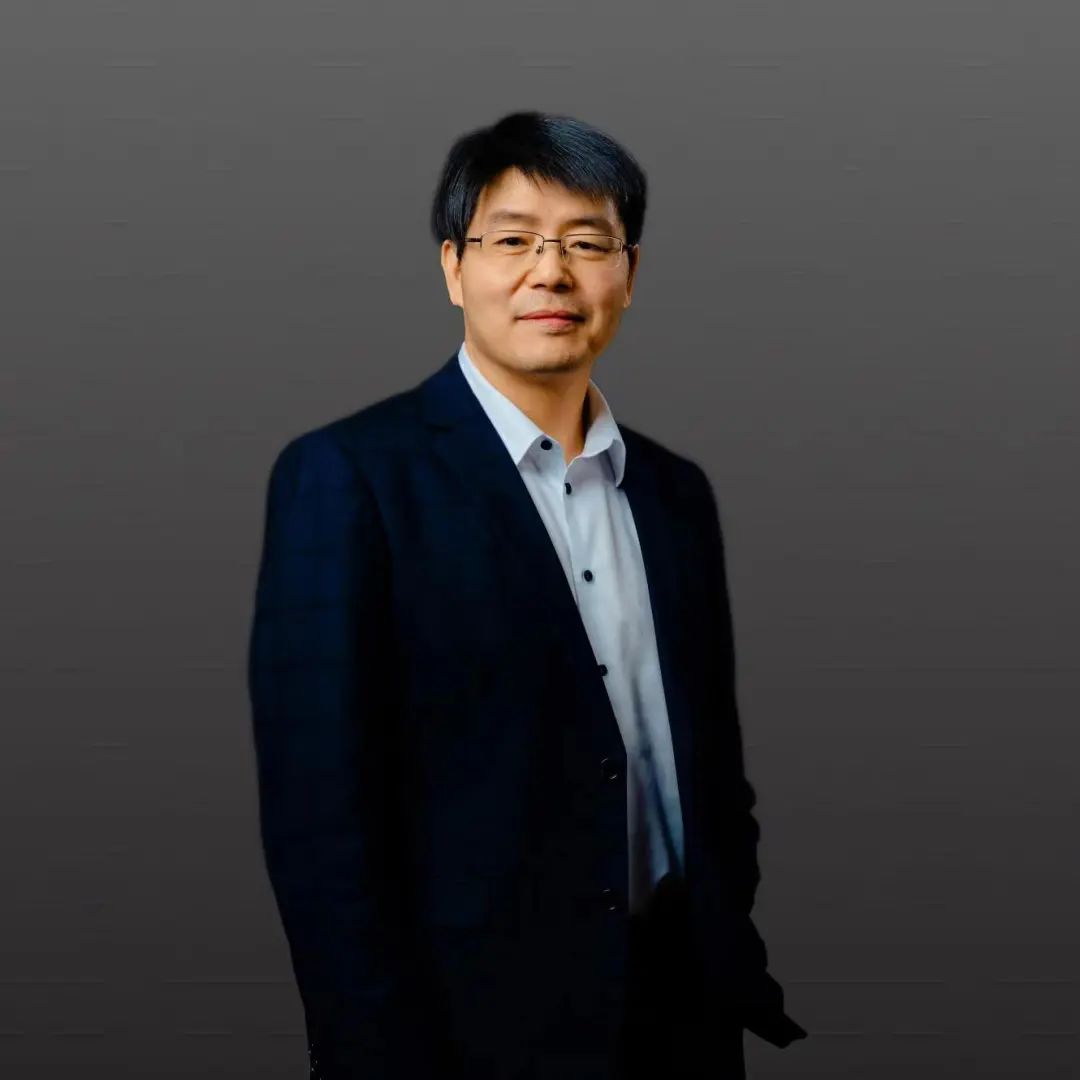
邵峰 炎明生物联合创始人、董事长
“我俩走到一起,是机缘巧合,也是水到渠成。”
从2015年开始,邓天敬在北京生命科学园区的CRO(医药研发外包)企业保诺科技担任CEO,每个月都在北京、上海、无锡,以及美国连轴转。2020年初,疫情让他被迫暂停,思考下一步要做什么。他想,要做真正的创新,做真正的新药。
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找到合适的原创研究和合作伙伴。对邓天敬来说,理想的合作伙伴具有三个条件:基础科学研究必须全球领先;必须具备转化成药物的可能性;合作伙伴必须有相同的想法和激情。
邓天敬偶然在C&EN杂志2020年2月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读到,炎症小体NLRP3抑制剂或成为战胜常见疾病的一种药物。炎症小体的发现人Fabio Martinon在文中提到:“2015年关于gasdermin-D和细胞焦亡的发现也许是天然免疫领域几十年来,甚至是到将来的最重要发现。”
这一发现正是来自邵峰。
同一时期,科学家邵峰正在不远处的北生所实验室埋头研究。从2005年回国起,邵峰先后研究了细菌感染、细菌免疫识别等领域,都取得了重磅成果。
2015年,他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院士。最近几年,他的研究重心转向细胞焦亡机制。
在炎症小体和细胞焦亡领域,邵峰走在世界最前列。他鉴定了多个针对细菌的胞内免疫受体,Gasdermin家族膜打孔蛋白的鉴定重新定义细胞焦亡,开辟了细胞死亡和免疫研究新方向。
2020年5月,经朋友介绍,邓天敬找到邵峰,最初的会面,话题很简单:中国创新药的下一步是什么?怎么做一个全新的公司?怎么投资中国的未来?从科学开始,他们自然而然地聊到了转化。
在邓天敬寻找合作伙伴之前,邵峰就在想转化的问题。
发表关于gasdermin-D和细胞焦亡的发现后,陆续有投资人找到邵峰做成果转化,他都拒绝了:一是邵峰认为自己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还需要时间挖掘其他重要的发现;二是邵峰希望能和一个真正有产业界经验的人一起做,少走弯路,能以最快速度推进项目。
2015年之后,邵峰几乎每一年都在细胞焦亡领域有新的突破,积累了更多靶点和研发思路。邓天敬找来时,直觉告诉邵峰,做产业转化的机会真的来了。
合作就此展开,邵峰负责科学和项目把控,其他的交给邓天敬。此后两年多,炎明生物从无到有,取名、注册、融资、建研发中心、推进管线上的一个个项目……
时势
核心人物一个是院士,一个是原保诺CEO,在中国创新药史上,这样的组合已经是第三次出现:
2010年,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与原保诺CEO欧雷强联合创办百济神州;201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与原保诺CEO崔霁松共同创立诺诚健华。这两个公司已成为中国生物医药领域标杆性企业。
人们难免将炎明生物与这两家公司比较。
“三家公司的DNA是不一样的。”在邓天敬看来,炎明生物和前两者有不同的核心竞争力和机会,百济神州和诺诚健华早期都选择在现有药物靶点的基础上研发更好的创新药,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炎明生物选择的是邵峰实验室的前沿科学发现产生的新靶点。
“时间也不一样。2010年以前,不可能做原研新药开发,因为源头创新需要科学,资源和时间。但像BTK这样的靶点可以比较快做出来,那时中国的新药研发能力只能支持做这样的新药,市场最需要的也是这样的产品。”
现在,随着国内原创研究的进步、技术平台和CRO的成熟、政府和资本对原始创新的重视,中国已培育出新药研发的成熟土壤。
这样的“天时”,加上生命科学园的“地利”,顶尖科学家的“人和”,做原创新药,“时势”已成。
时势,这是两人共同重视的东西。2005年、2006年,邵峰和邓天敬先后回国,成为较早归国的科学家。他们都相信,在充满机会和不确定性的中国,生物科技一定是下一个热点。
邵峰实验室发现的一系列与炎症小体或细胞焦亡相关的新靶点分子是中国的、原创的、世界领先的,把它做成药,最快的方式就是自己做。
炎明生物聚焦的领域均源自邵峰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围绕天然免疫,炎症小体和细胞焦亡前沿基础研究展开布局,建立了“细胞焦亡与先天免疫调控的分子开关”技术平台,精准操控细胞焦亡途径下的炎症反应,对其进行上调或下调,利用小分子和生物技术,开发相应的创新药物。
2021年1月,和玉资本、礼来亚洲基金、峰瑞资本、生命园创投、昌发展、博远资本以及青澜基金等多家著名投资机构,参与了炎明生物的首轮融资。
2021年7月,炎明生物北京研发中心正式启用。
2022年6月,炎明生物又在上海设了研发中心。另外,炎明生物还在美国圣地亚哥设有研发中心,以便未来在美国做临床。
三个中心同步推进,这与邵峰和邓天敬最初定下的目标有关——炎明在中国做成的新药,要摆上全世界的药架。
以下内容摘自经济观察报与邓天敬的对话:
研发构想
经济观察报:炎明的研发进展如何?
邓天敬:我们的执行力很强。研发进度比想象中快,项目比计划中多。公司以科学驱动,从靶点,到化合物,到产生数据,再做临床前或临床试验,再做转化,有很多可能性。
比如,我们现在有4个以上的靶点,都是邵峰实验室出来的、全新机制的。从生物学角度讲,这些靶点可从两个方向去调控免疫,调高或调低,抑制或激活。激活是所谓的把冷肿瘤变成热肿瘤,抑制跟炎症相关。这样,4个靶点就变成8个。每个靶点又可以有很多适应症,在N个疾病上有应用,那就是8×N,我们现在最强的是在早期的4×2,N端做不了那么多。
经济观察报:项目主要针对哪些疾病?
邓天敬:肿瘤和炎症性疾病。
比如我们在做脓毒症。每年有5000万人感染脓毒症,1100万人死于脓毒症,没有特效药,很多老年人因脓毒症去世。这是个巨大的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只要能把5%的脓毒症患者治愈,就为人类做了很大贡献。
再比如化疗。化疗很大的问题是耐受性,如果能减弱化疗的副作用,也能解决很多问题。我们的另一个靶点就是帮助解决这个难题的。
90%的疾病跟炎症相关,有很多的难治之症包括渐冻症,器官炎症,阿兹海默症等等,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科学去解决。怎么通过炎症的调控去找到解决疾病的钥匙?细胞焦亡和天然免疫调控非常前沿,国内国外都有人在做,很多中国公司也在立项,但确实不好做。
经济观察报:对后续的产业化、商业化有没有规划和构想?
邓天敬:能较快在临床上看到结果的几个项目,我们自己主推,推往临床二期以后,然后才有产业化的可能。
其他很多项目,做到一定时期可以跟跨国药企或机构合作,在不同阶段都可以合作,在某些领域,它们更有经验。我们做了一年半,现在已经跟很多大的跨国药企在接触了。
原创新药的项目在早期就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举个例子,炎症小体里有个靶点是NLRP3,2017年至今,很多公司在做,还没到临床就卖出去了,就在今年9月,美国一家企业Ventus Therapeutics的NLRP3外周抑制剂7亿美元卖给诺和诺德,首付款7000万美元。
经济观察报:你们如何构筑竞争壁垒呢?
邓天敬:我们的壁垒就是生物学的壁垒。
针对新靶点的原创新药开发,最重要的是能找到具有潜在成药性的第一个分子,而如何能找到这样的分子,依赖的是生物学的积累以及针对该靶点全面和深入的生物学理解。有人看到一篇文章,说做什么靶点好,也写明了筛选的方法。但其实研究过程中90%的内容是不会放到文章中的,失败的例子也不会放进去,他们不会知道为什么失败,坑在哪里,必须把坑都踩一遍。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项目本身就是壁垒。当然,我们也会把专利布局做到最好,争取每一个项目能领先未来的跟随者两、三年或更长的时间。
经济观察报:炎明与国外做原始创新的企业有什么不同?
邓天敬:美国的创新一大半来自biotech,它们看准好的科学,就把赛道最好的科学家、工业界专家找来,很多研发工作交给CRO做。
为什么这几年CXO这么火,这个模式能很快把一个主意变成一个东西。但大部分研发交给CRO也有很大问题,第一,做药是系统工程,如果都在外面做是永远形不成自己的战斗力的。第二,很难调动CRO的主观能动性来达到最大的效率和产出。
在炎明,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会一起讨论项目,不断碰撞,产生主意,然后执行,这样的思想碰撞在CRO公司是难以实现的。我们早期研发主要自己做,产出和效率也要比CRO高。
经济观察报:公司的名字和LOGO有什么寓意?
邓天敬:“炎”代表炎症,也代表中国神话故事里第一位“医药人”炎帝神农氏,寓意源头创新;“明”是清晰、明确,基于清晰的炎症反应(焦亡)机制,明确相关炎症疾病的治疗策略,又可作“日月阴阳”之解,寓意对人体免疫系统的上调或下调,这是我们的研发业务核心。
LOGO是我设计的,是一幅抽象的太极图,红色代表中国,蓝色代表世界,我们要从中国走向世界。点慢慢扩大,代表细胞焦亡的过程。
还有一句玩笑话,两个颜色就像邵峰和我,海水和火焰。这个LOGO代表了我们想做的原始创新,我们余生就要把这个事做成。
原始创新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必须做原始创新?
邓天敬:2006年我回国时,国内都做仿制药,甚至仿制药都做不好。2010年起,百济神州、贝达这批企业,把中国人做药的潜力发挥出来了,把做新药的能力打造起来了。2015年后,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毕井泉的改革,让跟随式创新走得很快,解决了中国人吃药难和药价贵的问题。这十年的红利,很多公司是受益者。
从市场和竞争角度讲,我们不可能总停留在针对中国市场做跟随式创新这个阶段,这也从股市上反映出来了。很多人都认为现在是生物科技的资本寒冬。怎么破局,必须有人来做全球首创,满足未被满足的重大临床需求,这个药必须是第一个在中国做出来的。
先发的商业优势很明显。比如用于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针对BTK靶点的小分子抑制剂,去年全球的市场销售是100亿美元,2013年首个获批的来自美国艾伯维公司的伊布替尼占了其中的96.83亿美元。
first-in-global(全球首创)有很多优势,有全球定价权,能做好医生教育。中国的生物医药行业的市场要做成和美国一样大,就必须要求这个行业能够不断做出这样的世界级的创新药,否则恐怕难以支撑中国生物医药创新的发展未来。
经济观察报:中国是否具备做原始创新的条件?
邓天敬:世界上最好的biotech有两个特点,产品瞄准first-in-global,创始团队有科学家的参与,有的得过诺贝尔奖,有的是医生,靠科学驱动。这两个特点能在最大程度上引导和助力研发活动,开发出前所未有的、具有重要临床价值的原创新药产品。
这样的公司,需要最领先的科学平台,中国虽然少,但有;需要钱,中国有;需要人才,中国也有顶尖的药研科学家。虽然最顶尖的医学转化方面的人才不足,但能做事的人才很多,而且中国人更有执行力,还有资源优势、政策鼓励。
在炎明,邵峰老师在项目科学上的参与度远大于国外同类公司的科学创始人。他的转化意识很强,科学家、医生也愿意跟他合作,让我们能在很早期链接医院的资源,能够找准临床的需求和疾病的生物标记物,这对早期研发非常重要。
经济观察报:做原始创新,生命科学园有什么优势?
邓天敬:这个园区代表中国生物医药创新的未来。
中国药物研发,最早是上海的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后来是苏州BioBAY,18A和科创板上市企业最多的就是上海和苏州这两个地方。
未来,做原始创新,北京应该具有后发优势,因为原始创新需要科学的源头,源头在高校、研究所、医院。北京也是创业的好地方,很多互联网公司从北京出来,这里的土壤更适合创新,人们大胆、敢突破规矩。墨守成规不会有创新。
从顶层设计上,政府希望有我们这样的企业出来,知道这是中国企业的发展方向。北京市、昌平区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经济观察报:怎么看当下市场的低迷?对炎明有什么影响?
邓天敬:在小环境,低迷能挤掉生物医药行业里的一些泡沫,是好事。受政策影响,中国的市场不像想象中大,当初PD-1预计每人每年会花费30万元,现在6万元,可能还要跌。跟随式创新科学上难度相对低一些,做不成药的风险也比较小,导致热钱都挤过来,大家做类似的项目,于是每个企业分到的商业回报自然就会小。现在股市的估值是在修正,当然,当前的大环境也放大了修正的程度。
在大环境,比如疫情、中美关系、美元升息、俄乌战争,叠加起来让大家没有信心。我觉得通过一两件事情,是可以恢复信心的,这样的事情未来任何一天都可能发生,行业将重回快速发展的态势。
从基本面的角度讲,要看大势。医药市场、创新药市场依然很大;中国有很大的空间要靠创新来弥补。这两个大势会使我们这样的公司受益。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好钱,备好粮,最关键的是要把价值做出来。
我们跟投资朋友聊,有的不知道现在的市场怎么回事,有人看好,有人保守。现在这样的形势对企业家是个考验,我们既需要坚持又需要保持灵活。同时也是考验投资人,能够深入理解生物医药研发行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内在逻辑,同时又能够准确和预见性地把握中国这个行业快速发展的方向和不断迭代的节奏,毕竟投资是投未来,不是当下。
